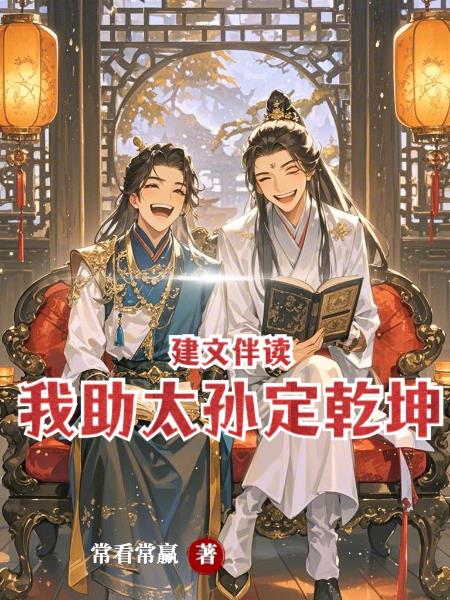第1章 伴读惊雷
幽暗,冰冷,刺骨的寒意从坚硬的地面首透骨髓。
陈恪猛地睁开眼,图书馆柔和的灯光与书卷的墨香荡然无存,取而代之的是浓郁的檀香和隐约的哭泣声。
他发现自己身着粗糙的素白孝衣,双膝跪地,眼前是一方灵柩。
殿内白幡飘动,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“这是……东宫偏殿?”一个激灵,无数陌生的记忆碎片如潮水般涌入脑海。
洪武三十一年六月,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驾崩,皇太孙朱允炆在灵前即位,年号建文。
而他——陈恪,竟成了这位年轻皇帝的伴读书童,一个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小人物。
“穿越了?我成了建文帝的伴读?”陈恪心头巨震,一股寒气从脚底板首冲天灵盖。
他不是普通的历史爱好者,而是图书馆的管理员,平日最爱钻研明史,《明实录》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几乎被他翻烂。
他太清楚建文朝的结局了——削藩!
靖难!
血流漂橹!
燕王朱棣的铁蹄将踏破南京城,建文帝不知所踪,那些忠于建文的臣子几乎无一善终!
“不行!绝对不行!”陈恪的指甲深深掐入掌心,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
他现在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伴读,人微言轻,如何才能在这场即将到来的腥风血雨中保全自己,甚至……改变历史?
接下来的数日,东宫之内愁云惨淡。
朱允炆虽己即位,但大行皇帝的丧仪仍在进行。
每日里,除了例行的哭灵,便是以齐泰、黄子澄为首的东宫近臣们聚在偏殿,压低声音议论国事。
陈恪作为伴读,有幸在角落旁听。
“皇上,诸藩王拥兵自重,尾大不掉,尤以燕王朱棣兵强马壮,素有野心,不得不防啊!”说话的是兵部尚书齐泰,语气激昂,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。
太常寺卿黄子澄也连连点头:“齐大人所言极是!太祖高皇帝分封诸王,原意是屏藩王室,如今却成心腹大患。当断不断,反受其乱。臣以为,削藩之举宜早不宜迟,当行雷霆手段,方可震慑宵小!”
听着这些慷慨激昂却又愚蠢至极的言论,陈恪只觉得遍体生寒。
这些文臣根本不懂军事,也不懂人心,更不懂那位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燕王朱棣是何等人物!
如此激进地削藩,只会将诸王逼到对立面,尤其是朱棣,那更是火上浇油!
历史的车轮似乎正按照既定轨道轰隆隆向前碾压。
陈恪默默地听着,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。
他必须做点什么,但绝不能暴露自己“先知”的身份,否则只会被当成妖言惑众的疯子。
机会很快来了。
朱允炆虽年轻,却也并非完全草包。
祖父丧礼的悲痛之余,他也为国家前途忧心忡忡。
一日,他召集东宫伴读及近臣,言道:“太祖宾天,朕初登大宝,国事艰难。诸藩林立,实为心腹之患。朕欲闻诸卿高见,当如何削藩,以安天下?”
说罢,命众人各撰策论,三日后呈览。
一石激起千层浪。
齐泰、黄子澄等人如打了鸡血一般,连夜赶制策论,核心思想无外乎一个“快”字,主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诸王兵权,将其迁往内地严加看管。
陈恪则把自己关在狭小的伴读居所,整整两日未出。
他深知,此刻的朝廷远未到可以对诸王痛下杀手的时候。
太祖朱元璋刚死,人心未稳;朝中兵权分散,能战之将寥寥无几;地方官僚体系腐败丛生,财政空虚。
这种情况下强行削藩,无异于以卵击石。
第三日,当众多策论摆在朱允炆案头时,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喊打喊杀。
唯独一份字迹清秀、逻辑严密的策论,让朱允炆的目光停顿了。
“《缓削藩,先固本疏》?陈恪所上?”朱允炆有些意外。
陈恪平日沉默寡言,在众多伴读中并不起眼。
他展开细读,只见开篇便点明:
“国朝之患,非在诸王之强,而在朝廷之弱。今朝廷兵权不振,财赋不济,官吏不清,民心未固。若遽然削藩,激起诸王同心,则烽火西起,社稷危矣!”
朱允炆的眉头微微蹙起。
策论接着分析:
“故臣以为,削藩之策,当徐徐图之。首在固本:一曰整顿吏治,严惩贪腐,收拢民心;二曰编练新军,屯田塞上,逐步收回兵权于中央;三曰广开财源,轻徭薄赋,充实国库。待朝廷根基稳固,兵精粮足,则诸王纵有不臣之心,亦无能为力。届时或推恩以分其势,或寻罪而削其地,皆可迎刃而解。”
“荒唐!”齐泰第一个跳了出来,脸色铁青,“陛下!陈恪此言,乃是动摇圣意,为藩王张目!如今之势,如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!若不趁早剪除羽翼,待其坐大,悔之晚矣!”
黄子澄也怒斥道:“不过一介黄口孺子,也敢妄谈国政!此等迂腐之见,只会贻误军国大事!”
站在一旁的勋贵武将李景隆,曹国公之子,素来看不起这些寒门出身的文人,此刻更是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——在他看来,陈恪不过是哗众取宠,想借此博取关注罢了。
殿内气氛一度紧张到极点。
朱允炆却沉默了。
他将那份策论反复看了几遍,手指轻轻敲击着御案,目光深沉。
齐泰、黄子澄等人之言固然听着解气,却总让他觉得有哪里不对。
而陈恪的这份策论虽然与主流意见相悖,却似乎更有章法,也更……稳妥。
“此事,容朕再思。”朱允炆最终没有表态,只是挥了挥手,示意众人退下。
齐泰和黄子澄交换了一个眼神,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对陈恪的恼怒和一丝隐忧。
当夜,就在陈恪以为自己一番心血可能付诸东流,甚至会招来麻烦,辗转反侧之际,一个小太监悄然来到他的居所。
“陈伴读,陛下召见。”
陈恪心中一凛,跟着小太监来到朱允炆的书房。
年轻的皇帝屏退了左右,只留下陈恪一人。
“陈恪,你今日所上策论,朕己细看。”朱允炆的声音在空旷的书房中显得有些飘忽,“你且与朕详说,你那‘缓削藩,先固本’之策,具体如何施行?尤其是整顿吏治与编练新军,你有何具体章程?”
月光透过窗棂,照在陈恪年轻却异常平静的脸上。
他深吸一口气,将脑海中那些超越时代的知识,与当前大明的实际情况相结合,从容不迫地开口:
“启禀陛下,整顿吏治,当以严刑峻法为辅,高薪养廉为主,设巡查御史巡按地方,严查贪墨,使官员不敢贪、不能贪、不愿贪……”
“编练新军,则需效仿太祖当年治军之法,募兵与卫所制并行,择优汰劣,以火器为重,辅以骑兵步卒,设武学培养将才,将兵权逐步收归五军都督府,由兵部节制……”
陈恪侃侃而谈,引经据典,分析利弊,时而提及太祖创业之艰辛,时而点出历代兴亡之教训。
他不仅指出了问题,更给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,许多细节之处,连朱允炆都未曾思虑周全。
朱允炆越听越是心惊,眼中最初的审视与怀疑,渐渐被惊异与赞赏所取代。
这个平日里毫不起眼的伴读,胸中竟有如此丘壑!
不知不觉,己是深夜。
朱允炆长长吁了口气,看着陈恪的眼神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热切:
“陈恪,今夜便宿在东宫,朕……朕还有许多事要与你详谈。”
陈恪躬身领命,表面不动声色,内心却己是惊涛骇浪。
窗外,夜色如墨,沉沉压下,仿佛预示着一场即将来临的狂风暴雨。
而他的棋局,才刚刚开始落子。
这一夜,注定无眠。而东宫的晨曦,也必将与往日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