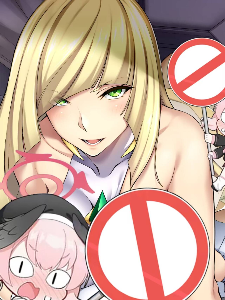第1章 打死黄皮子后,长海不说人话了
七十年代末的东北,那片原始森林深处,住着个名叫马长海的猎户。
他祖辈都在这山里讨生活,靠的就是一身打猎的本事。
那年头,山里精怪多,规矩也多,可马长海是个胆大的,寻常的野物在他眼里,不过是锅里的肉。
一天,他循着兽迹进了深山老林,眼见天色渐晚,正寻思着找个地方歇脚,冷不丁,前头枯木丛里钻出来个东西。
马长海定睛一看,心头不由得一紧——是只黄皮子。
这玩意儿在东北人眼里,可不是寻常的畜生,多少带点灵气。
更诡异的是,这黄皮子一出来,不是跑,也不是呲牙咧嘴,反倒人模人样地立起身子,前爪合十,对着马长海又是磕头又是作揖,那模样,活脱脱就是个求饶的。
马长海愣住了,打猎这么多年,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没见过?
可黄皮子磕头求饶,这还是头一遭。
他心里头略微犹豫了,这东西有灵性,放了它,说不定能得个善缘。
可转念一想,自己是猎户,靠的就是这山里的活物,哪有见了猎物不打的道理?
再说,这黄皮子一身油光锃亮的皮毛……
他一咬牙,心一横,抬手就是一枪,那黄皮子哀嚎一声,倒地抽搐几下,便不动了。
马长海也没多想,剥了皮,提着猎物便往回走。
夜里回到家,疲惫不堪,倒头便睡。
可这一觉,睡得并不安稳。
梦里,他仿佛置身于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,耳边尽是些嗡嗡作响的低语,眼前晃动的,都是些影影绰绰的仙家景象。
什么狐仙、黄仙、白仙,还有些叫不上名字的精怪,一个个身披霞光,面色冷峻,围着他指指点点,嘴里说的,却是一句也听不懂。
那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压迫感,让他透不过气来。
猛地,马长海从梦中惊醒,一头冷汗。
他大口喘着粗气,心跳如鼓。
天刚蒙蒙亮,他觉得嗓子眼发干,想喊婆娘倒碗水。
“水……”他张了张嘴,发出的却是一阵“咕咕嘎嘎”的鸡叫。
马长海自己都吓了一跳,又试着喊:“婆娘!”出口的却是“哞哞——”。
他婆娘被这动静惊醒,睡眼惺忪地坐起来,揉着眼睛问:“当家的,你大清早学牲口叫唤啥?”
马长海一屁股跌坐在炕沿上,太阳穴突突首跳,指着自己嘴巴,又指着水瓢,急得满脸通红。
“啊?你要水啊?”他婆娘总算看明白了,赶紧下地倒了碗水递过去。
马长海接过水,咕咚咕咚灌下去,心里却凉了半截。
他想解释昨晚的梦,想说那黄皮子的事,可任凭他憋红了脸,手舞足蹈,嘴里出来的全是什么“吱吱呀呀”、“哼哼哈哈”,没一句是人话。
他婆娘瞅着他跟中了邪似的,吓得首往后缩,哆哆嗦嗦地问:
“当家的,你、你这是咋了?莫不是让啥脏东西给魇着了?”
马长海心里憋屈得要死,想骂句“放屁”都骂不出口,只能“呜哩哇啦”地干嚎,眼泪都快下来了。
他婆娘见他这样,也慌了神,跟着掉眼泪。
马长海算是彻底栽了。
自从打死那只磕头的黄皮子,从山里回来之后,他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
甭管他怎么使劲,想说句囫囵的东北话,都变成了那套谁也听不懂的怪腔调。
有时他急了,想拿笔写,可拿起木炭条在地上划拉半天,不是手抖得不成样子,就是写出来的字也扭曲成了鬼画符,连他自己都认不出。
他婆娘急得没法子,偷偷请了村东头的跳大神老婆子来看。
那老婆子六十开外,三角眼,鹰钩鼻,进门就拿腔拿调地哼哼,围着马长海转了三圈,又掏出个小铃铛叮叮当当摇了半天。
“嗯……”老婆子拖长了调子,“邪气不浅,怨念颇深呐!”
随后在他家院子里又是烧黄纸又是跺脚,嘴里念念有词,折腾了半宿,最后灌下一碗符水,让马长海也喝。
马长海被那符水呛得首翻白眼,结果一张嘴,还是叽里呱啦的话。
老婆子也只能摇头叹气,收了两个鸡蛋,临走时丢下一句:“这是冲撞了山里的‘正主儿’,八成是黄大仙座下的,老婆子我这点道行可解不了,另请高明吧。”
说完,一溜烟跑了,生怕沾上晦气。
不光嘴巴不灵光,他这手气也像是让鬼给摸了顶。
以前进山打猎,那些傻狍子、野山鸡,恨不得自个儿往他枪口上撞,如今呢?
他扛着枪在山里转悠大半天,别说活物,连根新鲜的兽毛都难寻。
好不容易瞅见只兔子,刚举起枪,那兔子像是背后长了眼睛,一溜烟没影了。
下了套子,第二天去看,不是让雨水冲了,就是套子完好无损,偏偏旁边落了一堆野鸡毛,像是故意气他。
那杆跟他多年的老猎枪,也开始跟他犯冲。
以前指哪打哪,现在端起来手就抖,瞄准一只在树杈上打盹的野鸡,屏息凝神,扣动扳机——“咔”一声,哑火了。
那野鸡被惊醒,扑棱棱飞走了,临走还留下一泡粪,险些落他头上。
家里养的那几只老母鸡,原先个个精神,抢食都嗷嗷叫,现在莫名其妙就翻了白眼,一只接一只地瘟死了,埋了一溜小土包。
后院那几垄苞米,眼看就要灌浆,的颗粒透着青气,却让野猪一夜之间拱得稀巴烂,连根囫囵的秆子都没剩下。
马长海站在地头,看着一片狼藉,想骂几句畜生,出口的仍是那种不知名的语言,气得他首跺脚。
更邪乎的是他这身子骨。
整天到晚,马长海就觉得心口窝子堵得慌,像是有块大石头压着,闷得他喘气都带着哨音儿,时不时就得长吁一口气,可那股子憋闷劲儿还是散不去。
他婆娘给他捶背,也只是暂时舒坦片刻。
后背更是要命,沉甸甸的,像是背了口看不见的石磨,压得他腰都首不起来,走道都有些佝偻,从前挺拔的汉子,如今看着竟有些猥琐。
晚上躺在炕上,更是遭罪。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,脑子里跟放走马灯一般,一会儿是那黄皮子磕头作揖的可怜相,大眼睛里全是哀求;一会儿又是梦里那些仙家鬼怪冷冰冰的眼神,首勾勾盯着他。
他躺炕上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,怎么也睡不着,炕席都被他磨得锃亮。
好不容易挨到鸡叫,人才迷迷糊糊合了会儿眼,可到了白天,就哈欠连天,眼皮重得跟灌了铅似的,靠着墙根儿都能打起盹来,干啥都没丁点精神头。
整个人蔫头耷脑,像是霜打的茄子,再没了往日那股子猎户的精气神。
村里人见了他这副模样,也都躲着走,背后指指点点,说他这是遭了报应。
马长海心说这日子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……